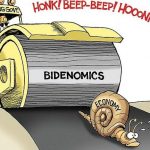現代好萊塢的根本且不可否認的趨勢是 製作討厭自己主題的電影,特別是當該主題源於傳統文化規範時。 目標是“解構”。一切都必須被解構、分解、燒毀,從公眾意識中抹去,並用“新的”覺醒理想取而代之。好吧,他們追捕芭比只是時間問題,結果令人尷尬。
由明星瑪格特·羅比製作、格蕾塔·葛韋格執導的《芭比》受到好萊塢影評人的喜愛,但他們的掌聲並不是圍繞故事的整體質量。 相反,它圍繞著被積極喚醒的消息傳遞。
邊緣 稱這部電影為:
“大膽的願景圍繞著解構芭比娃娃所代表的一些更複雜的現實的想法,以講述一個真正現代的女權主義故事。”
包裹 聲明:
“曾經是一個既令人著迷又充滿爭議的美泰玩具,讓人又愛又恨——一個細腰、空洞微笑、修長的娃娃,設計得像一個異性戀男性的幻想——現在是一個複雜的女權主義賦權象徵……”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 筆記:
“當芭比娃娃在現實世界中前進時,她必須應對作為人類的壓倒性情感和不適,以及使她成為自己世界中次要角色的父權制度。”
芭比娃娃的核心情節利用了女權主義中常見的“角色顛倒”概念,以及對男性和男子氣概的可預見的仇恨; 從一個女性掌控一切而男性只是“沒有代理權”的對象的地方開始。 肯是芭比控制的一個笨蛋,同時他也很殘忍,這是對“有毒的男子氣概”的經典喚醒描述。
但當芭比被傳送到現實世界(女權主義眼中的我們的世界)時,她遇到了卡通化的大男子主義和性別歧視,而肯則學會了熱愛父權制並試圖將其帶回芭比的世界。 獨立連線 斷言肯是故事中的反派,因為他摧毀了芭比娃娃的女權主義烏托邦:
“肯的回歸(我們敢說,是紅藥丸)的全部力量使一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利用他所有新發現的男性憤怒和父權權力來顛覆曾經由女性主導的田園詩。”
事實上,影片劇本至少使用了“父權制”一詞10次。 顯然,作為隱喻的前提是錯誤的,因為電影中描繪的動態對於女性來說並不存在,至少在西方社會不存在。 性別角色的存在是因為生物學,而不是因為陰謀。 但話說回來,終極的幼稚幻想不是芭比的夢境,而是女權主義的理想。

表面上的故事涉及到芭比的王國是一個與我們平行的宇宙,但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和恐懼開始侵入芭比的思想,她開始挑戰她所生活的世界的結構,同時擾亂每個人幸福的無知(這就是覺醒的活動家如何看待自己;作為救世主,讓人們擺脫由邪惡白人控制的幻想)。
毫不奇怪,這部電影也忽略了芭比娃娃作為玩具如此受歡迎的根本原因。
幾十年來,芭比一直是女權運動的主要目標。 他們指責該玩具強化了年輕女孩的負面形象,是“父權制的工具”,旨在將女性塑造成高不可攀的美麗標準和社會標準。 事實上,芭比娃娃非常成功,因為她是一張白紙——女孩和女人傾向於將自己的個性投射到虛構人物(以及許多其他事物)上,而芭比娃娃沒有明確的個性來阻礙。 小女孩們把芭比變成她們想要的樣子,通常就是她們自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聽到女權主義者認為每個人都需要在娛樂中“感到被代表”——除非她們能夠投射,否則她們無法建立聯繫。
但作為一張白紙,芭比娃娃這樣的玩具不可能有“操縱”或男性統治。 因此,女權主義主張不成立。 他們只是忽略了玩具對孩子的意義,只想到它對他們意味著什麼。
推而廣之,芭比電影中沒有浪漫,沒有芭比和肯的愛情故事,沒有過家家或照顧嬰兒。 小女孩用玩具做的所有事情都被故意從電影中刪除。 除了色彩繽紛的佈景設計之外,這部電影明顯反對它應該吸引孩子的想法。 它只針對一小部分人:極左思想家。
羅比將這個概念賣給了美泰公司,作為一部“熱愛芭比娃娃”但也“不迴避芭比娃娃周圍的問題”的電影。 既然這部電影已經上映,從美泰那裡得到誠實的意見會很有趣——這真的是他們的意圖嗎? 徹底解構他們的品牌? 這部電影甚至將美泰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威爾·法瑞爾飾演)描繪成一個憤怒的資本家,試圖迫使芭比娃娃“回到她的盒子裡”。
在電影中間,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在加州高中食堂裡對著瑪格特·羅比的芭比娃娃大喊:
“你代表了我們文化中的一切錯誤。 你們頌揚猖獗的消費主義,摧毀了地球……你們這個法西斯分子!”
這並不是對玩具的熱愛的表現,而是一群醒來的狂熱分子在做他們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們討厭這個產品及其代表的東西還不夠,其他人也必須討厭它。 女權主義者對自己瘋狂的信仰並不滿意。 只有當其他人被迫(通常是通過宣傳)確認這些信念時,他們才會感到滿足。